2018年4月29日
星期日 阴有小雨
龙凤村记
大理古城往东,沿途一路鸟语花香,攀在路边篱墙上的四季花团团如簇,舒展的枝条如同好客的主人张开了拥抱的双臂。阳光下生长的蔬菜出奇地肥美,池塘边便有许多采收完毕的妇人簇拥在一起洗菜,在行驶的车里都能闻到一股甜甜的葱白味道。相隔不远的田边,洗净的蔬菜被装上拖拉机,将带着洱海之畔的泥土芬芳运到不知名的远方。
我们在龙凤村北停车进村。我事先已在电子地图上查阅,通过这条与洱海平行的村街,可以把我们带到之前到过的才村、瓦村、小邑庄和北生久。但走在这条横贯南北的村道上,我却有些茫然,因为面对层峦叠嶂般的房舍,浑然一体的阵势,我居然是用了三个周末才走完。不知是否可以将之说成是一个村子,因为它已经确确实实合为一体,无可质疑的完整性,只有那些世居于此、上了年纪的老人,才可能清楚地记得那些早被时光淹没的虚无的界线。
一条枯河在这里改变流向,沿着村街向南流至村心,只见河边连续几棵低立的古杨柳,弯曲的柳条如同长长的卷发垂到地边,又被春风轻轻扬起。我一直觉得它是一种知觉迟钝的树种,此时湖边其他品种的绿柳早已枝繁叶茂,而它们似乎有几分矜持,叶蕊初绽,飘絮豆黄,有一种贵妇人的慵懒和倨傲。
进村后看到一两棵大青树,颇显伟岸。我一直觉得,除了村口横放的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石头,古树也是一个村落久远历史的最好见证。除了那些叹为观止的年代标识,我们会在树下歇凉的白发老人口里,得到更为久远的历史答案:“噢,在我小时候,就听当时九十多岁的太祖爷说,这棵树在他小时候就这么高这么大了!……”
老人一句话将一棵古树的历史拉到数百年外,我们似乎可以从那些枝叶上回溯更加久远的洱海沧桑。遗憾的是无论站在任何角落,我都无法留下一张较为贴切的照片,因为它不是被蜘蛛网一样密集的电线包围,就是被旁边的房子围得喘不过气来,空间太小无法扩张,那些伸向四邻或是往高处生长的枝条,已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斩断,使之如同扒在一张矮桌子上吃饭的大个儿,有一种伸不开手脚的局促。
巷子很深,楼房太高又让人感觉巷子太窄,有一两处塌墙上面长出了新的树木,如同一首无声的古曲,演绎着岁月的更迭。三月街临近,周末恰逢节假日,便有城里的小车开回来,停在房前屋后,村道便有些拥挤起来。有一辆车停在正在拆倒的房侧,很显然是主人借周末休息从城里回来重建新房,在盛年时完成一桩人生的要事。
在上周停住脚步的地方,我找到了才村完小右侧篮球场后边一个废弃的老院子,正东方有一幢古旧的砖瓦房,几乎可以断定就是那座承载着不屈民族之魂的西南联大教学楼旧址。可我却无法走得更近一些,因为校门口正躺着一条大狗,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立时翻身起来,隔着门栏昂起头来一动不动地盯着我,它那庞大的躯体像是一头强健的牛犊。这或许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条狗了,并且还是一条极有风度的大狗,不怒而威,不似别的小狗那般嘶天汪地、虚张声势,远远注视便让我感到胆寒,我只得绕开它的视线,悄无声息躲到东边它看不到的地方拍了张照片,便赶紧转身回来。
不知不觉走到了村巷深处的财神殿,高大阔气的山门给人别样的庄严感。我走到门口,发现侧门进去后是个停车场,一块村民委员会和一块老年协会的牌子让人知道这里还是办公场所。洱海沿岸,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。有时庙宇亦被建成高大阔气的钢混房子,打开寺门,最先看到的往往不是神坛和佛像,而是篮球场或健身器材。没有节庆、庙会和其他村民集会的时候,庭院大都充当停车场。有的庙子建得气势磅礴,楼下却常常作为村里集中办客的食堂,楼上才是远古神灵的所在,厢房或侧楼则是村民委员会的办公场所。有时在一个寺庙的门楣上,居然又挂上地方党委、政府颁发的“文明村”匾额,总之土地的集约化利用,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的“人神共居”格局。在我长久以来的意象中,神应该是沾满土气的,如今似乎也和我们一起“现代化”了,在高大敞亮的钢混楼房里,他们甚至还显得有些局促和猥琐,至少比不上孩子们熟悉的“变形金钢”和“钢铁侠”。说起这些,不知是否有一天我们会被孩子们追问得哑口无言。
绕过财神殿从另一条巷子往北走,一块宽敞的场地后面有一个坐西向东的寺院,山门上大书:洱水神祠。我同时看到了围墙上镶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识,旁边一口古井被锁上了沉重的钢门,不知道里面是否会有甘洌的井水,被保护的古井如今成了一个历史久远的标记。我点开手机一搜,得知洱水神祠是为纪念斩蟒英雄段赤诚修建的庙宇,唐时曾在此处建有临水亭,及至明代,还曾建有被称为“洱海四大名阁”之首的浩然阁。
千百年来,此处人文汇集,群贤毕至。特别是当初浩然阁建成之际,状元杨慎和挚友李元阳联袂前来参加落成庆典,让浩然阁一时声名鹊起。李元阳在其文《浩然阁记》中写道:“登阁而望,则见群峦洗翠,叠嶂吐云,夹涧之泉垂虹喷玉;而浮图绀寺,掩映于松杉之表。溪槃霞构,参差隐见,疑有隐君子在焉,可望而不可即也。”特殊的地理环境,使浩然阁视野开阔,登临其上,足可尽览苍洱风光。杨状元亦是诗兴大发,作《海风颂》,并写下《浩然阁舟泛同李仁夫作》:“莽苍野色杳无津,湖翠波光欲荡人。空籁迥闻王子吹,非烟遥起洛妃尘。明朝君上仙槎去,也忆狂夫梦海滨。”
两位大师皆属旷世之才,学养奇高,却都因清正耿直,刚正不阿,强权之下皆敢直言,结果仕途皆不得意。一人被贬谪,发配南疆;一人则看破官场黑暗,辞官退隐回乡,将40年余生寄情于故园山水。两个不得志之人,却在这边“蛮夷之地”结为良知,多年间一直结道交游,吟诗作对,忘情山水,成就一段极富意趣的人间佳话。两人足迹远播云岭大地,亦是三滇山水之幸,留下无尽诗文传唱至今五百余载,以至老少皆通、妇孺皆识。特别是状元杨慎,在阿来的《草木的理想国》里,亦曾对他的这一段经历专有一番赞叹:“从37岁遭贬到72岁去世,三十多年在云南设馆讲学,广收学生,而且还在云南各地游历考察,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,成就了涉及众多学科的学术著作。他以百科全书型的知识结构和不畏强权的人格魅力,使云南各族人民在杨升庵之后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原文化的巨大潮流。”
浩然阁建成数百年间,自然成为大理人文汇聚之所。清时素有“岭南第一才子”之称的宋湘及大理诗人沙琛、李蟠根等亦曾有诗文留存于此,以撰书成都武候祠“攻心联”著称的白族学者赵藩和西南联大教授游国恩均有游历。可惜时世变迁,胜迹空存,赵、游等人前来之时,浩然阁已不复存在。赵藩的一副对联写得意境悠远:“昆明池当属斯,仿凿习楼船,汉帝雄心驰域外;浩然阁已无存,搜遗补碑碣,唐人高咏表楹端。”如今,我所看到的也仅是洱水神祠前一个残留的座基,周边日益密集和不断加高的民居建筑,使这个狭小的地域变成一洞蛙井。咏叹赵藩等历代先贤的旧作,沧桑遗址给人无限感思。
一群骑着电摩托的学生娃在祠前小广场停车后,如同一阵风撞进银杏、缅桂和古柏环绕的院落,粗声大气地狂叫一通,吓得坐在北厢房台阶上的几位老人一阵慌乱,缄言不语,直待狂闹的孩子们走了,才战战兢兢地重新谝起断了几分钟的嗑子。我等到院内重新变得宁静之后,方才轻步走进古院,到大殿正中段赤诚的塑像前,虔诚地作了膜拜之礼,再慢慢离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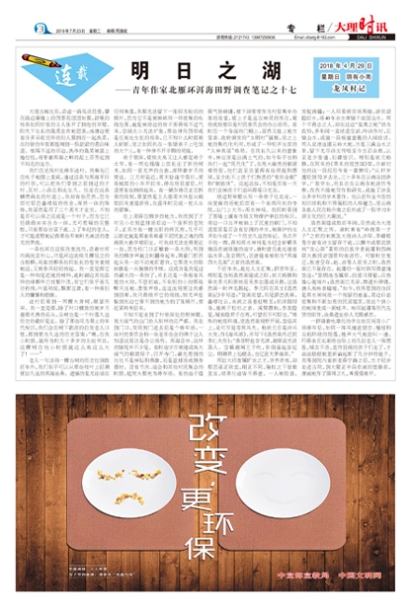
我要评报 隐藏留言须知
2.大理时讯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。
3.您在大理时讯留言板发表的言论,大理时讯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。
4.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 留言板管理员 或 大理时讯网络中心 反映。